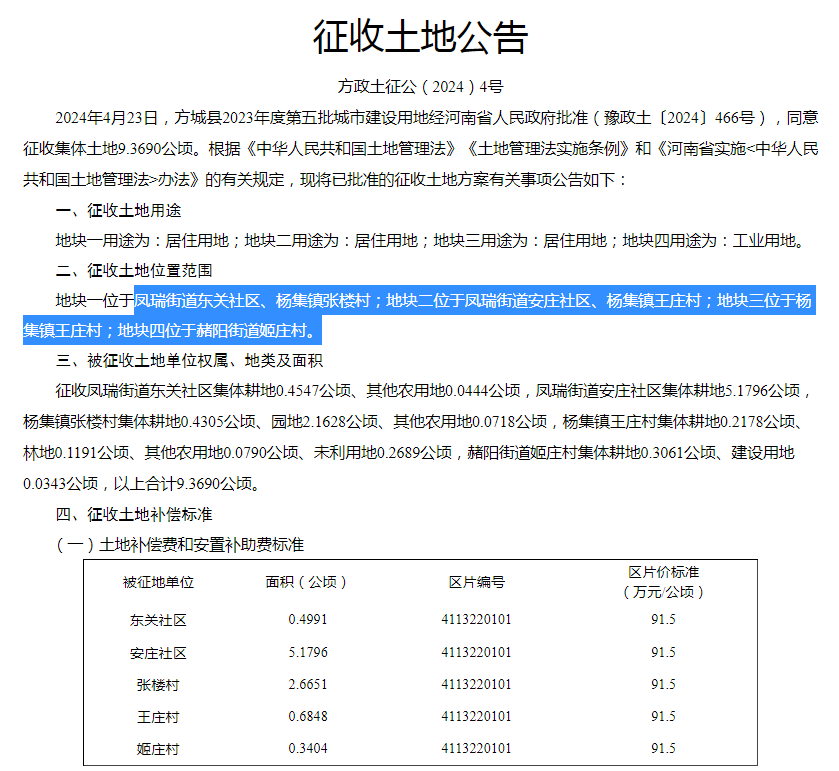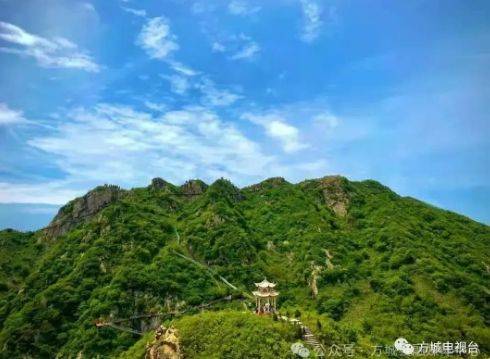在方城拐河的西北八里地有座山,过去南坡下有所大寺院。一股清凉的泉水,从寺内老佛爷的神胎下往外涌流。人们说这是宝泉,宝泉寺也因此得名。
传说很早的时候,有一年大旱,山上的石头都晒焦了。人们携儿带女到处逃荒。

有个叫韩石头的小孩儿,为了救活病瘫在床上的母亲,掂着瓦罐,满山遍野地给娘找水喝。由于天热,又渴又累,昏倒在山坡下。这时,从深山里出来一只老虎,把他噙到一眼泉水旁边。
韩石头醒来看见身边有眼清泉,先给娘打了一瓦罐,自己又咕嘟咕嘟喝个饱。掂着瓦罐往家走时,一路上高兴地喊着:“有宝泉了!有宝泉了!”韩石头这一喊,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都来这里打水渡旱荒。
有个姓权的老财主,看这是个发财的机会,说泉水出在他的地盘上,这是他的泉水,叫人们掏钱买水吃,又在井上修了一个佛爷神像。第二天,那老财主又来收水钱时,只见泉水已经干涸,以为是佛爷收去了泉水,因为有神像,他也没敢动,就悄悄走了。没想到穷人来打水时,泉水又流了出来。后来,人们集资修了一座寺院,取名“宝泉寺”。
据明代《嘉靖裕州志》记载:“普济寺,在宝泉山。旧名宝泉寺,宋(应为“金”)贞花(金宣宗年号)二年建。
大定(1161年~1189年,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初有广宫(公)和尚游于此,遂驻锡焉。国朝洪武三年(1370年)重修。俱有记。
”明代裕州(方城古称)参政许纶,在方城为政八年后枝临宝泉寺,感慨万千,留诗一首:“
八年无暇宝泉谋,此日登临惬胜游。
月影一瓢僧汲井,金声满座客输筹。
烟消黛泼山堆髻,花落红流水满洲。
自是此中消俗虑,不妨半日破民忧。”
同时代的裕州参政蔡志,在他眼中的宝泉寺,更是别有韵味:“
巡行遇晚到山间,借宿从林甚洒然。
绿竹满园节不改,黄花遍野景偏鲜。
耕耘自力尘无染,了见心田去外烟。
如命乐天穷奥典,悠悠自在度长年。"
宝泉寺当年盛况,从这两位方城主要官员的诗词中,可见一斑。
到了清朝末年,宝泉寺没能逃脱世俗的浸染,吸食鸦片的歪风邪气在僧人中甚嚣尘上,乃至寺院的田产屋舍,渐渐归属附近果木园村的陆姓大户人家。以前属于寺院的大部分土地被陆员外耕种,寺院的不少房屋也成了陆家户们的居所一一宝泉寺迎来了历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衰败。
新中国成立之后,宝泉寺只剩下了圣端和尚,和他师兄的徒弟同心和尚,二人在此苦苦坚守。那时的宝泉寺因年久失修,大部分屋舍进风漏雨,完全呈现出一派破败景象来了。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风暴,也没有因为“此中消俗虑”,而隔过了宝泉山。寺院里凡是能够用作“炼钢”的铁制品,悉数被收进了红彤形的炼钢炉里......就连宝泉寺的缔造者广公和尚,为了“肃静晨昏”,而亲手铸造的“大钟一钮”,也被附近韩沟村的朱家人套车拉走了。据说:途中运钟车辆翻倒在路沟里,朱家人空车而归;那口钟,自此却没有了下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公社食堂”散火后,拐河公社(镇)开始建设“拐河人民礼堂(现已不存在)”。宝泉寺为数不多的殿堂里的那些砖木,再度被大量“征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正值“文革”高潮,拐河公社开始修建黄土岗水库。此时,宝泉寺庙院里,只剩下满眼的断垣残壁,和历代留下的铭文碑刻,“异类”一般东倒西歪着,不知所措。成了亟待破处的“四旧”,它们连同寺院的基石、柱座、过门石等一道,搬倒或挖出后,被一车车运到了约三公里外的水库建设工地,成为了黄土岗水库400米大坝的底料基石,永远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
《普济禅院广公和尚影堂铭记》石碑,因为过于高大,幸免于难,无声地见证着宝泉寺的前世今生......如今,我们无从获悉圣端和同心两位和尚,目睹这一切时的内心感受。因为在社会ZY大改造的浪潮里,宝泉寺仅有的两名和尚也同样命运多舛:同心和尚先于师叔谢世,住在破庙里的圣端老和尚,也成了宝泉寺村的“五保户”,84岁时郁郁而终(生卒年不详)。
自此之后,宝泉寺不再是一座名冠中原的古刹名寺,而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山间村落了......
版权声明:文中部分图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来源:方城县融媒体中心